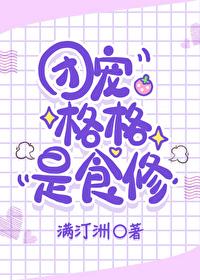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扶苏穿成宋仁宗太子 > 120125(第15页)
120125(第15页)
后年及笄,也就是今年才十三岁。扶苏牙酸了一下:十三岁啊,在现代还是刚上初一的小女孩,但在早婚成为风俗的后代,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准新娘了。
如果是别人,扶苏会劝她珍重身体、嫁娶自由的话,那么苏轼的亲姐姐的婚事,他是决计要阻拦的了,就算沾染上因果也在所不惜——历史上的苏家阿姊,可是嫁到了程家后,被婆家兼姨家人折磨得不轻,年纪轻轻,不到二十就去世。
一条好端端的人命摆在眼前,沾染些因果又有何妨呢?
扶苏提笔就写道:没错,你做得很对!女子们的闺阁时光本来就无比珍贵,带她来汴京见见世面没什么不好的。说句不好听的,以后在婆家就未必有那么舒心的日子过了。
对了,你阿姊今年十三的话,和我阿姊妙悟的年龄相若,要不要我从中搭桥,介绍她们两人认识认识?说不定很谈得来呢!
写完这一封给苏轼的之后,扶苏又飞快地另起了两张信纸,收件人的署名分别为“娘娘”和“妙悟阿姊”。
娘娘,阿姊,别睡啦,来活啦!-
眉山,苏家。
自从五年前,苏家蛰伏养望的当家人苏洵和其长子苏轼同榜中试之后,苏家就从眉山本地的书香门第之一,一跃成为望族。逢年过节,本地的县令都会特地登门,客客气气地送上年礼。
而苏洵的夫人程夫人并未随夫入汴京,当官太太。她的小儿子苏辙在本地的书院随大儒读书,不好轻易迁动。女儿又许了娘家的侄子,未来会嫁在眉山,程夫人干脆就留在了本地,操持起家务,抚养一儿一女。
其实,程夫人留在本地,还有一个原因。是她的女儿苏轸私底下求了她:“因阿爹与阿弟在京中做官,程家虽然上门贺喜,其旁支却有人说闲话,说我苏家恐嫌贫爱富,退婚另择佳婿。”
“若您也北上,无人坐镇,留我一人在眉山看护幼弟……只怕流言更会不知传成什么难听的样字了。”
程夫人沉默了一下:“都是旁支拈酸的闲言碎语,轸儿,你莫要挂怀。”
但她还是接受了女儿的建议,留守坐镇眉山,流言果然稍有止歇。
但近些年,渐渐又有些弹压不住了。
原因为何?竟是出在全家都引以为骄傲的苏轼身上。苏轼和当朝太子同出国子监、同榜中试,彼此因为知心的友人,这在朝堂上根本不是秘密。
且不说他自己,年仅十三岁就登上了《求知报》的编辑一栏,引得眉山学子人人自豪。光说苏洵吧,因他是太子挚友之父,官场上也甚少引来交恶,堪称平步青云。
可以说,有子如此,苏家未来的前程,远远不止一个眉山。
压在苏轸身上的流言,反而重了起来。虽然她和表兄许了亲事,但除了自家人外,几乎人人都默认她要退婚,上京择一良夫的。就连和她青梅竹马长大的表兄,通信时也饱含讥嘲,说自己不过是井底□□耳,配不上堂堂天鹅。
苏轸收到信件后,哭了一整夜。
这件事,她对谁都没说过,只每日随着程夫人学习出嫁的仪程。直到京中阿弟寄来的一封信再次打破了她好不容易建设好的平静。
阿弟的信上说道:阿姊,掐指一算,你马上就要出嫁了,但是还没来过汴京呢。也不知道未来姐夫有没有那个能力让你去,不如趁着闺中时刻,让阿爹和弟弟带你来玩啊!
母亲把这封信给她看:“轸儿,你是怎么想的呢?”
苏轸沉默了良久:“阿娘,我想去。”
“你姨母那边呢?恐怕一听闻你要去汴京,又要说些难听的话……”
苏轸的神色狠狠动容了一下,旋即恢复了平静:“阿娘,我想去。”
“……”
程夫人幽幽一叹:“罢了,阿娘知道了。”
半个月后,一顶小轿之中,一位容色清丽、年至豆蔻的少女用手指剥开车帘,隔着窄窄的缝隙,一切未曾想象过的景象如流光般掠过眼帘。少女被过量的繁华骇得一惊,飞快地掀下帘子,片刻之后,又心痒痒地撩起。
原来,这就是汴京。
与眉山殊无一丝相同之处。
当初阿爹、阿弟上京游玩时,目睹的就是眼前的盛景吗?
苏轸放下帘子,把世界隔绝在外,眼光流连在自己素色的衣衫与绣鞋上,身子瑟缩了一下,只觉与外界格格不入。
轿子摇摇晃晃,不知走了多久,苏轸只觉外间人声渐渐稀疏,心中紧张不已。
“到了。”轿夫说道。
过了片刻,轿中踏出一个少女,她咬着嘴唇怯怯看向宅邸。一切都是陌生的,唯有牌匾上的“苏”字,让她熟悉而亲切。
阿爹和阿弟就住在这里。
苏轸思及于此,顿时推门而入,那看似厚重的门板竟然很快被推开,她甚至没觉得自己使了多少力道。
苏轸正觉得奇怪,门后突然出现了一张她熟悉又陌生,见之感怀无限的脸。
“阿姊,欢迎来汴京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