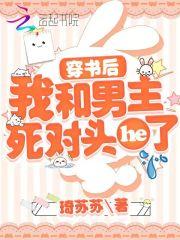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出宫前夜,疯批帝王后悔了 > 第491章 盼君归(第2页)
第491章 盼君归(第2页)
“我不需要懂统治。”她缓缓举起铜镜,“我只需要懂人心。母亲临终前最痛的,不是被背叛,而是发现她信任的人,亲手喂她吃下遗忘的药。她说:‘我宁愿清醒地死,也不要糊涂地活。’”
镜面微光一闪,忆鉴晶石随之共鸣。刹那间,冰牢内光影交错,浮现出一幕幕画面:太后生产当日血流成床,裴世衡端药走近;少年陆沉跪求饶命,却被拖入地道;年幼的晚芜抱着母亲哭喊,却被强行抱离……
裴世衡惨叫一声,抱头蜷缩:“关掉!关掉它!我不想看!”
“你不想看?”晚芜逼近一步,“那你为何要看?为何要记录?为何要把这些全都锁进地宫,妄图让后人永远无知?今天,我要让你亲眼看着,每一个被你毁掉的生命,如何重新睁开眼睛。”
她转身离去,身后传来凄厉嚎哭,夹杂着断续呢喃:“对不起……婉儿……我真的以为……你会感激我……”
走出地牢,天色已暮。晚霞如血,染红整座骊山。程砚等在出口,低声道:“刑部拟议,明日公开宣判。你可愿亲自主持?”
她颔首:“我要在传音塔前。”
翌日清晨,长安城万人空巷。传音塔广场上竖起高台,四方百姓齐聚,手持写有“我记得”三字的竹简或布条。钟鼓齐鸣,百官列班,太子亲自迎请晚芜登台。
她立于高处,身披素色深衣,背后悬着一面巨大的空白卷轴。风拂动衣袂,她开口,声音通过传音塔扩散至七十二州:
“今日,我不宣判任何人死刑。因为真正的惩罚,不是剥夺生命,而是面对真相。”
她挥手,忆鉴晶石悬浮空中,光芒洒落,空白卷轴上渐渐浮现文字??那是由千万人记忆汇聚而成的《贞元纪事录》,详述二十年来宫廷秘辛、冤案始末、权力倾轧。每一段落下,便有一束光升腾而起,直入云霄。
“从今往后,每年今日定为‘真语节’。凡此日,无论贵贱,皆可登上传音塔,诉说心中所知。若有隐瞒、篡改、打压者,举国共讨之!”
台下寂静片刻,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。老人流泪,孩童拍手,书生振臂高呼:“还我清明!还我真实!”
就在此时,遥远天际忽现异象??原本晴朗的天空裂开一道缝隙,金光倾泻而下,照在言魂花海上。那一片枯萎已久的花田,竟在同一瞬间全部复苏,绽放出湛蓝花瓣,蕊中传出的不再是遗言,而是歌声、笑声、婴儿啼哭、恋人絮语……
程砚仰望苍穹,喃喃道:“这是……忆鉴之力彻底觉醒了。”
晚芜闭目感受着空气中流动的记忆波纹,忽觉胸口一热。忆鉴晶石轻轻震动,内部那两个并肩小人影,竟缓缓分开,其中一个转身向她挥了挥手,然后化作点点星光,消散于风中。
她知道,那是陆沉最后的告别。
数月后,新修的皇家书院落成,名为“明鉴堂”。堂前立碑,刻着一行大字:
>“宁听一句真话,不闻万句颂歌。”
阿阮成了第一批入学的学生。她每天背着书篓蹦跳上学,总爱指着墙上挂着的《补遗卷》插图说:“这是我姑姑,还有我哥哥,还有程叔叔,还有赵爷爷……他们都是英雄。”
晚芜则搬出了皇宫,在铃屋旁建了一座小型档案馆,收集来自各地的民间证词、口述历史、遗书残稿。她不再称自己为公主,也不接受任何封号。人们私下唤她“持鉴者”,但她更喜欢阿阮给她取的名字??“说真话的姑姑”。
某个春夜,她独坐灯下整理一份来自岭南的旧信。写信人是一位盲眼老妪,说她儿子因传播《实录》残篇被处决,临刑前高呼:“我虽死,但我记得!”她请求晚芜将这句话收入馆藏。
晚芜提笔抄录完毕,忽听窗外铃声轻响。她抬头望去,只见月下花影摇曳,似有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言魂花丛中,手持陶埙,唇边含笑。
她没有起身,也没有呼唤,只是轻轻说道:“哥,今晚的风很暖。”
那人影微微颔首,旋即淡去,如同晨雾融于朝阳。
第二日清晨,阿阮跑进屋嚷道:“姑姑快看!后山那棵老梅树开花了!可去年它明明已经枯死了!”
晚芜随她来到山坡,果然见一树雪白梅花凌寒绽放,枝头挂着一枚小小的铜铃,随风轻晃。
她伸手触碰花瓣,忽觉一阵暖意顺指尖流入心间。忆鉴晶石再次发光,映出一行新浮现的文字:
**“有些爱,比死亡更长久;有些真相,比王朝更永恒。”**
她仰头望天,云卷云舒,仿佛听见无数声音在风中低语??
“我记得。”
“我没有忘记。”
“我要说出来。”
铃声悠悠,不绝于耳。
叮铃??
叮铃??
叮铃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