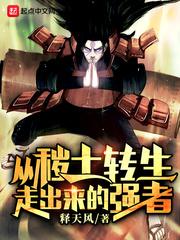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柴刀流漫画大师 > 第138章 实验连这也要做求月票(第1页)
第138章 实验连这也要做求月票(第1页)
刚过早上八点,坂本健就出门了。
这个时间,助手们以及加治编辑都还没来,原本他应该要等到大家都来了才走的。
但仔细一想,这么些天里,似乎已经美绪和春奈她们跟踪过几次了,要是稍晚点出发,刚好遇。。。
夜风从山脊滑下,穿过驿站老旧的木窗缝隙,在“足迹号”车厢内掀起一阵细微的震颤。感应毯边缘微微泛起蓝光,像是回应那远方雪地上的脚步声。铃木仍坐在车顶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录音机外壳上那道细小的裂痕??那是三年前在北方小镇,被冻僵的手掌不小心磕在铁栏杆上留下的印记。
千夏已经睡下,外套还搭在他肩头。他没有动,只是望着星空,任寒意一层层渗进骨头。他知道这不该是放松的时候。“足心计划”第二阶段启动在即,十二个疗愈站选址尚未敲定,百名导师培训课程大纲还在草稿阶段,而直播信号昨天刚接入教育云平台,技术团队连夜调试了七次才让步态数据可视化模块稳定运行。
但他此刻不想看文件,也不想开会。
他想听风。
风里有声音,不是言语,而是节奏。枯叶擦过树皮的沙响,雪粒坠落屋檐的轻叩,远处溪流在冰层下缓慢奔走的闷鸣。这些声音曾是他童年唯一的陪伴。父亲早逝后,母亲在纺织厂轮三班,他一个人守着空屋,夜里总把耳朵贴在地板上,听整栋楼的人回家:高跟鞋急促敲击楼梯是加班归来的会计,拖沓的脚步混着咳嗽属于患关节炎的老教师,还有隔壁小男孩蹦跳着跑上楼时那欢快得几乎要飞起来的步伐。
那时他就知道,人走路的样子,藏着比语言更深的秘密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是阿米尔发来的定位共享请求,附言只有两个字:“等你。”
铃木回了个“好”,随即关机。他知道阿米尔不会催,就像北极的极光从不着急照亮大地。他们之间不需要太多话。当年在冰原营地,两人并肩行走三天两夜,全程没说超过十句话,却完成了最完整的步序共鸣训练??那种无需语言的同步,才是真正的“同行”。
他缓缓起身,赤脚踩上车顶金属板。刺骨的冷立刻顺着脚心窜上来,但他没退缩。这是他自创的“清醒仪式”:每当思绪混乱或身体疲惫时,就用最原始的方式接触世界。金属板的纹路硌着足底,像一张粗糙的地图,标记着他走过的每一道沟壑。
他开始走。
慢,稳,呼吸与步伐同频。一步六秒,和拓也在孤儿院走廊里学的一样。投影仪自动感应启动,淡绿色轨迹在他身后延展,如一条蜿蜒向远方的小径。AI提示音轻轻响起:“检测到使用者处于低体温状态,建议终止户外活动。”他按下静音键。
走到第十圈时,感应毯突然波动。车内系统捕捉到了异常频率??有人正在靠近驿站,脚步沉重,间歇性停顿,右腿落地明显滞后。
铃木停下,凝神倾听。
不多时,木门外传来迟疑的敲击声。三下,间隔均匀,力度克制。
他披上外套,走下梯子开门。
门外站着一个穿旧军大衣的男人,约莫五十岁上下,脸上刻着风霜的沟壑,右手拄着一根磨秃的登山杖。他的左腿小腿处缠着厚厚绷带,隐约渗出血迹。
“你是……铃木老师?”男人声音沙哑,“我叫川岛,是个护林员。本来想去下一个镇上找医生,但暴风雪封了路。我看见这里有灯,能不能……借宿一晚?”
铃木侧身让他进来,顺手接过他肩上的背包。重得惊人。
“你背着什么?”他问。
“土。”川岛喘着气坐下,“从我家后山挖的。她说过,要是哪天她不在了,就把这土撒在老橡树下。”
铃木没再问。他知道有些话,要等到脚步愿意先开口时才会说出来。
他为川岛处理伤口,发现是陈年旧伤复发,肌肉萎缩严重,若不及时干预,可能面临截肢风险。千夏被吵醒,帮忙打了点滴。两人交换了个眼神,都明白这不是普通旅人。
凌晨两点,川岛终于退烧,靠在沙发上,盯着感应毯发呆。
“你们这个东西……真能听懂人心?”他忽然开口。
“不能听懂。”铃木倒了杯热水递过去,“但它能让心自己说话。”
川岛沉默片刻,脱下左脚的靴子和袜子,露出变形的脚踝。他深吸一口气,将脚踩上感应毯。
投影骤然变红,节奏断裂如碎玻璃。数据显示:左腿承压仅12%,重心长期偏移导致脊柱侧弯达18度,步频紊乱源于持续性神经痛。
“你不是今天才受伤的。”铃木说。
“十三年了。”川岛苦笑,“那次雪崩,我背她出来,砸断了腿。可她还是没活下来。”
车厢一下子安静下来。窗外风声呼啸,仿佛无数亡魂在林间穿行。
“她是我妻子。”川岛低声说,“也是这片区最后一位森林教师。孩子们管她叫‘树语者’,因为她能教他们听懂树叶说话。火灾那天,她冲回去救一个被困的学生……火太大,屋顶塌了。”
铃木闭上眼。他想起了梨奈站在舞台中央张开双臂的画面,想起了小舟第一次听见“爷爷叫我”的泪水,想起了拓也画出那条绕过雪山回家的小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