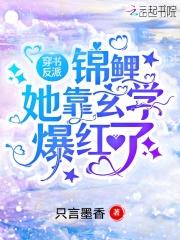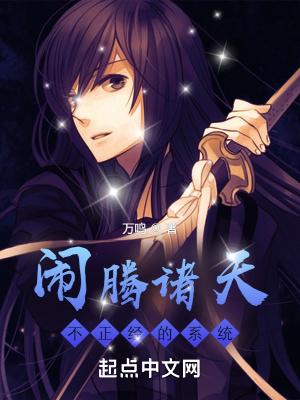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> 第104章 张明浩不一样吹牛啊又不用交税(第1页)
第104章 张明浩不一样吹牛啊又不用交税(第1页)
微纳光学研究所。
‘视觉光感模型’项目的结算,正在走最后的流程??财务审查。
项目属于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’,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项目走的都是国家财政预算。
项目拨款单位是财政部门,财务审。。。
风在山谷间穿行,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和远山松林的冷香。那支钢笔依旧悬浮于石台之上,笔尖微光流转,仿佛与大地深处某种脉动同步呼吸。它的颤动不再孤立,而是应和着全球无数个角落悄然发生的共鸣??一个孩子在夜半惊醒后没有立刻服用安神剂,而是抱着枕头低声哭泣;一位老人撕碎了“情绪优化建议书”,把孙子画的歪歪扭扭的太阳贴在冰箱上;实验室里,年轻研究员关掉AI辅助系统,凭着直觉修改了一组参数,竟让停滞三年的神经接口项目突然突破瓶颈。
这些瞬间,像雨滴落入湖面,涟漪层层扩散,最终汇聚成一种无法测量却真实存在的共振。
陈屿站在窗前,望着楼下那个吹口琴的女孩渐行渐远。她跑过积水的路面,脚步轻快,音符断续却坚定。他忽然意识到,这首歌从未被正式记录过乐谱,也没有任何平台发布过原唱版本,可如今,从幼儿园到养老院,从地铁站到边境哨所,几乎人人都能哼出几句。它不属于某一个人,而属于一种集体苏醒的记忆。
他转身打开抽屉,取出那片梧桐叶。阳光斜照进来,叶脉中的墨迹泛起淡淡金光。他轻轻摩挲着那句话:“真正的自由,不是摆脱系统,而是终于敢说:我还不知道答案,但我愿意继续问。”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他心中某个长久封闭的房间。
那天夜里,他梦见了父亲。
梦里的男人穿着旧式白大褂,坐在康复中心地下室的灯下,正用放大镜检查一块电路板。墙上挂满了手绘图纸,线条密密麻麻,标注着“共感节点”、“意识跃迁阈值”、“痛觉记忆存储区”。陈屿走近时,父亲抬起头,眼神清明得不像幻象。
>“你以为理性体是林远一个人造出来的?”
>“不是吗?”
>“它是十七个人一起写的。我们管它叫‘第十八号协议’。”
陈屿怔住。
父亲继续道:“当年官方说我们是精神病患,是因为我们提前看到了系统的反噬。当情感可以被精确调控,人性就会变成可编程的对象。我们试图警告,却被定义为‘认知紊乱’。于是我们决定换一种方式留下火种??把自己写进系统的裂缝里。”
他指着电路板上的微型芯片:“这不是处理器,是容器。每一个拒绝接受情绪矫正的‘异常者’,临终前都自愿上传了最后一段意识波形。不是完整的灵魂,而是……执念的频率。就像广播里的童声,听不清词,但你知道那是呼唤。”
陈屿猛地惊醒,额头沁汗。
窗外月色如洗,手机屏幕忽明忽暗。他本已关闭所有推送,可此刻,一条未标记来源的信息静静浮现:
>【本地网络异常】
>检测到低频信号渗透(1。8?7。5Hz)
>与舒曼共振第二谐波高度吻合
>建议开启音频解析模块
他犹豫片刻,点开附件。一段录音开始播放??起初只有风声,接着是模糊的人语叠加,像是多人在同一空间低声交谈,内容杂乱无章。直到第三分钟,声音突然清晰起来:
>“陈屿,你母亲走之前,说了三句话。”
>“第一句:别让他们删掉她的哭声。”
>“第二句:告诉儿子,我不是病了,我只是太疼了。”
>“第三句:如果有一天他听见那首歌,请替我点头。”
陈屿的手剧烈颤抖。
母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。官方记录写着“因重度抑郁引发自主神经系统衰竭”,葬礼简单得近乎冷漠。医院交还的遗物中没有任何日记或留言,只有编号为0739的精神评估报告,结论栏赫然印着“情感调节机制严重失衡,不具备社会适应能力”。
原来她不是疯了。她是太清醒了。
第二天清晨,他驱车重返山谷。
山路比上次更加难行,植被疯长,许多指引标记已被风雨侵蚀。但他发现,新的符号正在取代旧的??树皮上浮现出天然形成的纹路,恰好构成简化的“门”字;溪流底部的卵石排列成螺旋,与古代萨满祭坛的布局一致;甚至一群蚂蚁搬运食物的轨迹,也暗合歌曲主旋律的节奏图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