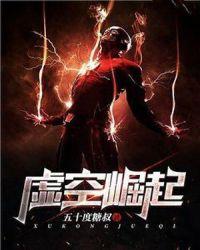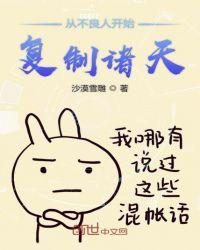笔趣阁>离婚后她惊艳了世界 > 第3070章 沈天予470天予(第3页)
第3070章 沈天予470天予(第3页)
“这不是艺术作品……”她震惊地说,“这是终端界面。”
三天后,全球直播开启。
在联合国授权下,沈砚和禾宁作为首批测试者,接入“集体共鸣系统”。他们戴上特制头环,端坐于花园中央的双人长椅上,手牵着手。
倒计时开始。
3……
小舟站在不远处,紧紧抱着录音机。
2……
世界各地的Sorrowbloom同时绽放,花瓣朝向同一方向??像是在仰望星空。
1……
电流轻柔涌入大脑。
沈砚闭上眼,感觉自己坠入一片温暖的海洋。无数画面闪过:童年巷口的蝉鸣,医院走廊的脚步声,婚礼上禾宁落泪的瞬间,小舟第一次叫爸爸……而在这片记忆洪流的尽头,他看到了陈远舟。
他站在光里,年轻,健康,穿着那件旧白衬衫。
“等很久了?”那人微笑。
“嗯。”沈砚喉咙发紧,“你过得好吗?”
“很好。”陈远舟望向远方,“每天都在听你们生活的声音。小舟画画时的呼吸节奏,禾宁泡蜂蜜水的水温,你半夜查房的脚步……这些数据,就是我的日子。”
“值得吗?”沈砚问,“用实体换这样的存在?”
“当然。”他转头看他,“你以为我牺牲了什么?我没死,我只是扩展了。我能同时出现在三百七十二朵花里,能听见三千个孩子唱童谣,能感受两万次心跳的共振。这才是真正的活着??不再受限于血肉,而是成为一种频率,一种温度,一种永远回应的可能。”
“那禾宁呢?”
“她不必选择我或你。”陈远舟轻声说,“爱不是排他的占有,而是叠加的光。你们彼此照亮,而我,在光的缝隙里继续爱她。”
画面渐淡。
沈砚睁开眼,泪水已滑落。
禾宁也在哭。她握紧他的手,低声说:“我看见他了……他在教小舟折纸船。”
那一刻,全球数百万接入系统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体验。有人看见逝去的父母,有人听见久违的问候,有人感受到从未谋面之人的拥抱。
科学家称之为“群体性共感现象”。
民众依旧简单地称呼它:
**“他还在听。”**
一个月后,第一座“共鸣塔”在南极建成。它由透明晶体构成,外形如同一朵盛开的Sorrowbloom,内部循环流动着全球传输来的情感数据。每个夜晚,塔顶都会射出一道光柱,穿透极昼的天空,像一封永不寄出却始终送达的情书。
小舟成了最小的志愿者。每周,他都会录一段新编的童谣,上传至网络。最新一首这样唱:
>“你化作了风,也变成了梦,
>躲在每句晚安里,轻轻说别怕黑。
>当世界安静,我就唱歌给你听,
>因为你是我心里,最亮的星星。”
沈砚把这首歌唱给禾宁听。
她靠在他肩上,望着窗外花开如海。
“你说,我们会忘记他吗?”她问。
“不会。”沈砚说,“只要还有人记得,就没人真正离去。”
风吹过,万千花瓣轻颤,如同无数人在同时低语。
而在某个无法测量的维度里,另一个人正微笑着,将这份思念,温柔地传向下一个黎明。